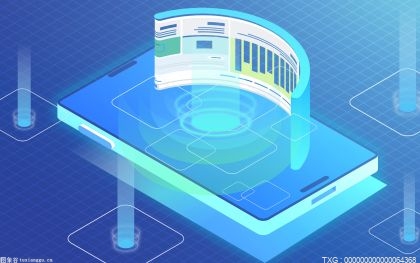摘要:文章从数字经济的协同渗透效应和挤出效应出发,结合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利用2016—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相关数据,验证了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适度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并以此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且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关键词: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区域异质性
引言:近年来,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等信息通信技术高速发展,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数字经济的衡量测度、发展路径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1,2]。从经济形态出发,政治经济学认为数字经济具有可持续性[3]。数字经济通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长尾效应等对企业生产效率、产业结构、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产生显著影响[4]。从微观企业层面出发,学者们分别从经典企业管理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关系嵌入视角出发,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管理、企业价值、企业生产率、企业转型等方面的影响[5]。例如,何帆和刘红霞(2019)[5]通过对国内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增强创新、降低成本等方式实现数字化变革,最终发挥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作用。从宏观经济层面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改变劳动力就业结构,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两端极化”需求格局[6];同时,数字经济可能增加开放型经济复杂性,引起世界市场同质化及逆向全球化等负面效应[7]。从博弈论角度出发,许恒等(2020)[8]提出数字经济具有技术溢出效应和技术冲击效应,借此构建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非对称竞争博弈模型,认为“竞合发展”政策有利于创新和社会利益均衡。从实体产业角度出发,数字经济为制造业转型提供强劲动力,以制造业数字化为起点,以数据、创新、需求和供给为路径,逐步实现实体经济数字化、产业结构高级化[9]。石涌江(2021)[10]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出发,认为数字经济发挥协同效应、成本节约效应、价值创造效应,对制造业产业升级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单门槛效应。肖远飞和周萍萍(2021)[11]认为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速产业升级,并以此为中介实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就区域经济层面而言,部分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创新绩效,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存在区域异质性[12]。然而,亦有部分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例如:姚志毅和张扬(2021)[13]发现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是周期性波动的,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显著为负,已产生“挤出效应”;姜松和孙玉鑫(2020)[14]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呈“倒U”型曲线关系,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根据现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等可能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积极影响;与之相反,数字经济的自我膨胀性和挤出效应可能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那么,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到底是发挥协同渗透效应还是挤出效应?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路径为何?厘清以上问题有利于对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路径进行合理规划,有利于提升落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实现经济均衡发展。本文提出数字经济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模型,通过对2016—2019年31个省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1研究假设
 (资料图)
(资料图)
1.1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
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其网络特性,自身需要投入大量财力和人力资源。技术创新具有高投资、高风险特征,同样需要投入大量财力、人力和社会资源等;同时,研发创新还需要一定的周期实现收益。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其对该区域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发展,企业会不断通过高额投资和技术创新获得市场优势,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逐步得到体现。数字经济作为重点发展方向,研发资金和人员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数字经济边际收益不断提高,对数字经济产业的技术创新发挥直接的促进作用,并通过溢出效应逐步向相关产业和传统产业传导,对区域内产业整体技术创新水平起到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时代,边际收益递增导致“强者恒强”的现象普遍存在[15]。因此,当数字经济经过萌芽期和高速发展期,发展速度和规模逐渐趋于稳定时,容易出现寡头或者垄断现象,数字经济的自我膨胀性得到更多体现,广大企业对头部企业高度关注并快速模仿跟进,头部企业从技术创新中获取的实际收益可能低于其研发创新的成本。因此,可能导致企业研发创新积极性降低,则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减弱。据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呈“倒U”型曲线关系,相比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适中的地区,若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过高或过低,则区域技术创新水平较低。
1.2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
在传统工业经济发展时期,企业受生产、库存、管理、交易成本等多方面因素限制,以追求长期平均成本最低值为目标来确定最优生产规模,帕累托提出的二八定律得到普遍认可[16]。对数字经济而言,根据梅特卡夫法则,随着网络规模扩大,网络价值不断增大,相比于传统工业经济而言,数字经济的规模经济效应更加显著[17]。同时,长尾理论认为众多小市场的集合具有与主流市场相同的能量,当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范围、增加产品种类时,会引起研发、服务、财务、市场等方面成本降低,实现范围经济效应[18]。由此可见,数字经济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实现协同渗透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数字经济创造的价值相比于其投入而言是十分有限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随着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传统的实体线下市场可能受到极大冲击,导致用户向数字经济网络进行转移,也使得高度依赖于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企业和行业面临巨大威胁。同时,传统的工业经济也可能受到数字经济的巨大冲击,数字经济企业不断占有市场,通过不断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来减少来自中小企业的竞争,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降低。据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2: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呈“倒U”型曲线关系,相比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适中的地区,若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过高或过低,则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较低。
1.3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随着自然资源不断消耗,人类环保意识逐渐增强,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实现碳中和及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供给角度出发,第一,技术创新可以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材料利用率等方式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第二,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个人或企业更加容易通过网络获取先进知识和技术,技术溢出效应发挥更加显著,从而引起产业结构高级化并对传统产业起到提升和带动作用。从需求角度出发,技术创新能够通过提高底层人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来拉动内需,实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19],还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并形成累积效应[20]。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过低或过高时,企业关注点更多在于占领市场、获取高额利润,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由此可知,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呈“倒U”型曲线关系,且数字经济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因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3: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倒U”型曲线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呈“倒U”型曲线关系,并进一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形成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倒U”型曲线关系。
2研究设计
2.1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对我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进行研究。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来自历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17年首次),故面板数据期间为2016—2019年。区域经济增长相关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为避免极端异常值造成的回归曲线扭曲问题,更加准确地反映变量间实际关系,参考文献[21],对全部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缩尾处理,分别替换为百分位数1%和99%对应的数值。
2.2变量定义和测度
被解释变量:区域经济增长(REG),采用省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解释变量:数字经济(DE),采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衡量。中介变量:技术创新(TI),采用研发强度进行衡量。控制变量:为准确评估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控制以下可能影响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因素,选取人口增长率、地方财政支出、教学科研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第三产业占比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人口增长率(POPGR)采用各省份当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衡量;地方财政支出(PUB)采用各省份当年一般财政支出的对数值衡量;教学科研财政支出(DESC)采用各省份当年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财政支出的对数值衡量;固定资产投资(FIX)采用各省份当年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对数值衡量;第三产业占比(THIRD)采用各省份当年第三产业产值占该地区GDP的比重衡量。
2.3模型设定
根据研究假设,需要验证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Baron和Kenny(1986)[22]所提出的传统的三步法无法准确揭示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中介效应,因此,本文借鉴Edwards和Lambert(2007)[23]提出的一般分析框架中的调节路径分析方法进行假设检验,构建如下回归模型:Y=α1+α2X+α3ME+α4MO+α5X´MO+α6ME´MO+ε(1)ME=β1+β2X+β3MO+β4X´MO+φ(2)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区域经济增长),X为解释变量(数字经济),ME为中介变量(技术创新),MO为调节变量,且在本文中,MO与X为同一变量(数字经济),X´MO为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的二次项,ME´MO为中介变量(技术创新)和调节变量(数字经济)的交互项,ε和φ为残差。
3实证结果与讨论
3.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其中,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6.04和80.40,均值为30.87,标准差为15.49。由此可见,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
3.2回归结果与讨论
为确保模型可靠,避免伪回归,采用HT检验进行短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其中,REG、POPGR、PUB、DESC通过检验,全部变量的一阶差分值通过检验由于上述一阶单整变量的存在,采用Kao进行协整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对于模型(1)和模型(2),ADF检验结果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此外,为确保无重要变量遗漏,对残差序列进行白噪声检验,Q统计量的P值均大于0.05,结合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模型设定合理。模型(1)用以检验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模型(1)可以检验调节变量数字经济与解释变量数字经济交互项、调节变量数字经济、中介变量技术创新以及调节变量数字经济与中介变量技术创新的交互项间的总效应,即检验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回归结果见下页表5。列(1)至列(3)以技术创新为被解释变量。列(1)中只包含可能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加入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得到基本线性回归模型列(2),表明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1241)。在列(2)的基础上加入数字经济的平方项,得到非线性回归模型列(3),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平方项与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1038)。据此,可以看出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呈“倒U”型曲线关系,支持假设1,即当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过低或者过高时,对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非常有限。当数字经济发展到适当水平时,对技术创新具有较强促进作用。数字经济的发展本身即蕴含着大量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萌芽时期,网络规模和影响力相对较小,因此,对相关行业和传统工业行业的带动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对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是十分有限的。随着网络规模倍增,用户数不断增加,数字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数字经济向传统工业经济不断渗透,实现产业数字化,发挥新技术、新业态的积极影响,以数字经济的发展加强相关产业和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提高社会整体技术创新水平。随着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关企业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获得市场份额,形成寡头甚至垄断市场,产生较高的市场进入壁垒。此时,广大中小企业和传统工业行业都无法从市场中获取利润,难以维持高额的研发投入,数字经济的自我膨胀性和挤出效应则会发挥主导作用,社会整体技术创新水平普遍受到抑制。列(5)至列(6)以区域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在列(4)的基础上加入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得到基本线性回归模型列(5),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2514)。在列(5)的基础上加入数字经济的平方项,得到非线性回归模型列(6),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平方项与区域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1301)。综合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呈“倒U”型曲线关系,支持假设2,即当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过低或者过高时,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数字经济的适当发展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当数字经济处于萌芽期,实际效益尚未得到充分显现,且受认可程度较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有限。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作为新的技术和经济范式,数字经济能够有效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并实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结构被改变,新技术、新业态都对传统行业造成一定的威胁和负面影响,可能对传统行业和实体工业经济形成挤出效应,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消费者福利受损,引起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在列(6)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技术创新,得到列(7),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2674),数字经济的平方项与区域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1473),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再次验证。在列(7)的基础上加入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得到列(8),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具有权变影响。综上可以看出,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其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支持假设3。数字经济不断发展,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通过网络资源实时掌握用户需求、优化产品,改变传统经营模式,提高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提高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水平,并通过渗透效应向周边行业和传统行业进行逐步传导,从而提高各个行业技术创新水平。然而,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过高,且远超于当地工业经济发展水平时,传统工业经济实体企业处于显著劣势地位,二者之间差距过大使得数字经济的自我膨胀性和挤出效应发挥主导作用,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不利影响。
3.3稳健性检验
由于我国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差异,故对东部地区省份样本和中西部地区省份样本分别进行检验。其中,东部地区包含11个省份,共有样本44个。中西部地区包含20个省份,共有样本80个。通过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子样本分别进行检验,来验证上述结果是否稳健。中西部地区样本回归结果见下页表6。列(2)中,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1024),列(5)中,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亦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1948)。分别加入数字经济的平方项得到列(3)和列(6),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平方项与技术创新不相关,与区域经济增长不相关;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仍保持显著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1149和0.2127)。在列(6)的基础上先后纳入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的交互项,得到列(7)和列(8),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均显著正相关,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与区域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1034)。上述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相对较低,随着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得到更好地体现,表现为“倒U”型曲线的上升部分。下页表7是东部地区样本的回归结果。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1381),数字经济的平方项与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1402)。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2114),数字经济的平方项与区域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上述结果表明,对于东部地区样本组而言,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均呈“倒U”型曲线关系,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再次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4结论与建议
4.1研究结论
本文验证了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以及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从理论上看,本文明晰了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根据创新经济学理论和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从实践上看,本文为揭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推动区域数字经济的合理化发展、坚持以创新为本拉动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文得到结论如下:第一,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均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当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过低或者过高时,该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均较低。表明数字经济存在门槛效应,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一个区间,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超出该区间时,数字经济的自我膨胀性和挤出效应则会凸显,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降低。第二,技术创新发挥中介作用。随着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水平得到提升,并逐步向其他行业实现技术渗透和外溢,从而有效提升全社会技术创新水平,并以技术创新为媒介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新业态,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显著高于该地区其他产业发展水平时,数字经济的垄断特征加剧了产业间的鸿沟,技术创新的渗透效应受到阻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抑制。第三,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仍处于发展初期阶段,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发挥显著促进作用,即为“倒U”型曲线上升部分,且技术创新发挥正向调节作用,随着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得到更好地体现。而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均呈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4.2对策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地方政府应加快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引导企业之间共享数据、平台等各种网络资源,实现共享经济;加速实现产业数字化发展,通过在研发创新、生产经营、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为传统产业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使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地方政府应通过数字经济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融合,实现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政府应加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引导,提高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以此带动技术进步和区域经济增长。对于东部地区,尤其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应增强对技术创新的激励,避免企业盲目追求短期利益,实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第二,制定并落实财税优惠和人才引进政策。首先,地方政府应积极为数字经济相关企业提供工商管理、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减轻企业发展初期面临的财税负担;其次,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创新性人才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加强财政支出向研发创新和教学科研的倾斜,助力高校培育人才;最后,地方政府应加快制定并落实人才引进政策,从落户、创业补贴、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多方面为高端技术型人才扫清后顾之忧,实现培育人才、留住人才,从根本上为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第三,加强对数字经济产业头部企业的监督引导。由于数字经济存在自我膨胀性,数字经济产业极有可能出现一家或少数几家头部企业形成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发展态势,对中小企业形成打压,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地方政府应从法律角度和行政监管角度出发,加强对头部企业的监督,防止形成头部企业对市场的垄断。同时,地方政府应积极制定相应引导政策,促使头部企业坚持走创新发展的道路,带动广大中小企业和相关周边产业的共同发展,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张路娜,胡贝贝,王胜光.数字经济演进机理及特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21,39(3).
[3]荆文君,孙宝文.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经济学家,2019,(2).
[4]戚聿东,肖旭.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J].管理世界,2020,36(6).
[5]何帆,刘红霞.数字经济视角下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评估[J].改革,2019,(4).
[6]阎世平,武可栋,韦庄禹.数字经济发展与中国劳动力结构演化[J].经济纵横,2020,(10).
[7]龚晓莺,王海飞.当代数字经济的发展及其效应研究[J].电子政务,2019,(8).
[8]许恒,张一林,曹雨佳.数字经济、技术溢出与动态竞合政策[J].管理世界,2020,36(11).
[10]石涌江.产业化、生态化和数字化:三化融合的思考[J].科学学研究,2021,39(6).
[11]肖远飞,周萍萍.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和面板门槛效应实证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1,35(3).
[13]姚志毅,张扬.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联动性的动态分析[J].经济经纬,2021,38(1).
[14]姜松,孙玉鑫.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2020,41(5).
[19]湛泳,徐乐,王恬.包容性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研究——基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视角[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7,29(1).
[20]李四维,傅强,刘珂.创新驱动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收敛:基于空间计量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2020,34(6).
[21]祝树金,汤超.企业上市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20,34(2).
作者:马嫣然 吕寒 蔡建峰 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经济金融学院 西北工业大学
标签: